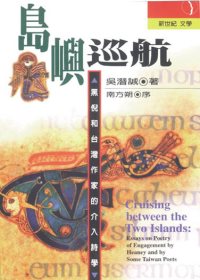
書名:島嶼巡航:黑倪和台灣作家的介入詩學
作者:吳潛誠
ISBN:9789578453753
出版:立緒
___
內容簡介:
吳潛誠教授承繼對愛爾蘭文藝復興脈絡的熱愛與嚮往,探討當代諾貝爾文學獎薛摩思.黑倪的介入(engagement)詩學。黑倪被譽為北愛爾蘭災厄的見證者、愛爾蘭靈魂的歌手,與偉大詩人葉慈一樣,曾經擺盪在社會責任和追求藝術自由之間,嘗試探討北愛爾蘭之紛擾的來龍去脈,以詩的文學性涉入對現實政治的關懷,而在世界文學中佔有一席之地。
作者進而將焦點停聚於同是島嶼的台灣文學作家,如詩人李敏勇、江自得、李魁賢、楊牧、陳黎、林燿德等人,將政治情境引人聯想的兩個島嶼上的創作,以黑倪的介入詩學為主軸,一一剖析論述,表達對這些作家勇於介入公眾議題的肯定與建議。
會看這本書是因為我想找黑倪(Seamus Heaney)的詩來看,卻找不到書,搜尋的過程中意外發現有文學評論,就有了這麼難得的相遇。
作者的文字優美,語氣平和,儘管談論的是「有人遭受苦難,吟詩豈非罪惡?」這樣的困難問題,依舊展現出優雅氣度,層層推進自己的剖析與觀點,閱讀完心情平靜且帶著希望。(很少有書可以讓我有這樣的感覺,珍惜這樣的閱讀體驗)
D*
___
(p.7-8)
南方朔〈序〉愛爾蘭文學啟示錄
繼《航向愛爾蘭》,這一次,吳潛誠教授更清楚的將他的航向轉換為對台灣文學的反省。這次他談的不再只是認同,而是政治與因政治而引發的受苦,而參考座標則是九五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黑倪。而其論旨則是:在這個充滿悲傷和受苦的世界,詩人究竟能夠拯救什麼?在社會責任與藝術水準的追求間,詩人如何將兩者的衝突轉化為一種更高的價值?在這個問題上,吳潛誠教授所碰觸到的,其實已不僅僅是愛爾蘭或台灣,而是更重要的當代主要文議題之一了。
政治的不義,社會的迫害,受苦,長期以來即始終為文學主要關切對象之一,它可以表現為指控、揭露,或激昂的反叛與憤怒,而另外,它也可以沉澱為傷痛的回憶,甚至昇華成為人類基本情境的反省等,由於歷史情況不同,我們其實很難界定出那一種思考或表達方式最為妥切。而當巨大的受苦降臨,或政治巨變,文學的脆弱遂使它很容易就被淹沒。黑倪就曾指出過,在這個創痛與受苦的世界,詩只不過是纖弱的花朵,它究竟能為這個世界做些什麼?它要如何才顯得不是一種奢侈的多餘?甚至於,文學還可以被這樣的質問:在歷史中,徘徊在公眾價值與美學價值之間的文學藝術,它所處的乃是一種不自在的情況,寫作的邊界應被如何設定?
而義大利的卡爾維諾對此倒是有過非常基本而深刻的討論。他在《文學之用》論文集裡指出,文學經常面臨著兩種難題:一是公眾的價值意圖指令或兼併文學的價值,而另一則是文學拒絕公眾的價值,而退縮到純屬自為的天地中。卡爾維諾指出,無論政治的兼併、文學的亢奮,都是將眼前短線的政治考量看得太過優先,政治過度自信的另一側面,所顯露的其實也是一種恐懼,政治害怕文學藉由語言和論述提供出一種與它不同的思考方式。至於文學完全的抗拒政治與社會的現實,並退縮到孤立的空間裡,則將使文學本身成為一種無知。這兩類情況只會出現壞的政治與壞的文學。他深信,文學的看與說,和公眾觀點的看與說並非完全相同,因而可以揭示出許多不同的觀察與批判的角度,而將問題設定到更普遍的人類經驗中。當文學如此的自我期許,文學與政治的緊張不自在,遂有可能被扭轉到一個更有綜合性的價值中。因此,文學和政治皆然,都必須同時對自己有自信和不信,讓這種緊張又自在的關係長存。
p.2
一九六九年,北愛爾蘭境內的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爆發衝突以後,黑倪這位已積極介入著稱的詩人,曾在〈感覺進入文字〉(一九七四)中提到那事件對他創作的影響:
從那一刻起,詩的問題從單純的獲致較人滿意的語文聖像(verbal icons)的事情,移轉到尋找適合我們之困境的意象和象徵。
p.10-11
文人的贖罪心理不難理解,另一個著名的例子發生在醫生作家契可夫身上。一八九○年,契可夫在文學創作和社會地位兩方面皆已卓然有成,卻突然決定長途跋涉,前往遠東的沙卡林監獄島,和囚犯同住,進行訪談,並記錄他們的生活狀況,然後整理成書出版(即《沙卡林島》一書)。沙卡林島是一座魔鬼島,拘禁的是重刑犯、政治犯、暴動分子等等社會「敗類」。契可夫所以會有這個「奇怪」的決定,一方面因為他一直矢志為一個良善而有正義的未來而效力;另一方面,則想藉此旅行,驅逐自己身上殘留的祖父的農奴血液,獲得心理和創作上的自由解放。黑倪同時把這件事寫成〈契可夫在沙卡林島〉一詩。
契可夫本人形容這趟旅程在償付「虧欠醫療的債務」。作為醫生,幫人解除病痛,理所當然有權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毋庸另外證明;相對而言,當世界上還有許多人尚得不到自由,正忍受種種折磨,自己卻「不務正業」,從事藝術演練,豈非形同對生命的冒犯?是以,契可夫覺得,必須有所證明,方可心安理得地投入奢侈的藝術創作。
契可夫動身出發的前夕,他的莫斯科友人送他一瓶高級白蘭地作禮物。這趟舟車勞頓的艱苦旅程歷時六個星期,契可夫一直留著那瓶酒,直到抵達沙卡林島的第一個夜晚,才開瓶暢飲。
黑倪說,他常常把契可夫開瓶的剎那當作深具象徵意義的一刻:「作家正在享受琥珀色澤的白蘭地。」契可夫一上岸以後,便得以實際聽見囚犯身上的鎖鏈所發出的叮噹聲響,「在周匝瀰漫著迫害氣息和殘酷音樂當中,他品嘗著濃郁的醇酒和奢華放縱。」
p.12
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認為,戰後波蘭詩人的任務是「從歷史的災難中搶救兩個詞:正義與真理,缺少這兩個詞,所有的詩只是空洞的遊戲而已。」是以,赫伯特自己的作品捨棄抒情,稱頌實實在在的生命,反對輕浮的、遠颺的藝術幻想。但赫伯特並不反對藝術可以享有它的權利,只要它知悉本身的限制。他在一首詩中寫道:「欣賞詩吧,只要你不把它用作現實的逃避。」
p.23
黑倪絕對不是那種奢談超越現實的詩人;但他大概會同意前輩大師葉慈所界說的:藝術,不是行動,而是「現實之一靈視」(a vision of reality)。
(中略)
藝術源生自現實,但又不與現實完全脗合一致,而是針對現實提出對立的批判或詮釋,投射一想像的視域。
p.47
李敏勇一向都是勇於介入的詩人,不會有閃避現實,沖淡醜惡的嫌疑。(事實上,黑倪也曾攻擊有人想把詩人當作另一個世界的隱士,或當作自外於族群的閃避者。)他的問題只剩下以什麼態度來看待他所發現的醜惡。黑倪在〈史帖信島〉的第八部分陷入困惑,在結尾部分卻祭出前輩大師喬哀思,發表對立看法,他告訴黑倪:
……「你的責任
不為任何普通儀式所解除……
第一要務就是寫
為喜悅而寫……
放縱,起飛,遺忘。
你已經傾聽夠久了。現在,敲打你的音符。」
p.80-82
我常常提倡地誌詩,雖然這並非尋常可見的詩類。花蓮縣立文化中心出版的《花蓮現代文學選:詩卷》中選了很多詩,有的可能純粹因為詩本身的價值而被收入,有的顯然因記載地方,跟花蓮的關係密切。
我們生長在土地上,土地就在我們腳下,與我們關係密切。但「地誌」其實只是一個符號、標誌,是等待詮釋的。我們應該知道定義常常不屬於被定義的對象,例如地理條件本身,而是屬於下定義者。也就是說,地理現實是等待詩人╱書寫者賦予意義,透過藝術的創作使它有形有狀,而顯示出意義。把花蓮、台東稱作後山,說台灣孤懸海外一隅,把某個地方叫北濱或南濱……這都是從特定的立場所作的詮釋。
陳黎的詩〈花蓮港街‧一九三九〉中提到的朝日通後來變成軒轅路、入船通改成了五權街……台灣所有的街道都被賦予政治意義:中山路、中華路、莊敬路……這些路在台灣任一城市中都有,政治無所不在。其實,花蓮有花蓮的山水,但山水要有人詮釋。我小時候遊澄清湖,有個標語讓我印象深刻:「春風吹得遊人醉,莫把斯湖當西湖」。這標語帶有一層毋忘在莒的意味——澄清湖也不錯,但切勿流連忘返,應該記得西湖才是最美好的。從前文人來到台灣,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說這裡「男無情,女無意﹔鳥不語,花不香」;清朝詩人寫道:「破夢無名鳥,傷心未見花」。台灣不是沒有花,而是蠻夷之邦的花,在中國古典文學裡找不到的的花。英國統治者到了澳洲,見其風景類同英國,但又不如英國。這是把台灣、澳洲視為他者 ( the other),用來襯托本身的存在及偉大。相對於殖民帝國,被殖民者就是他者。
地誌詩是中古世紀拉丁文裡就有的一種詩類,十八世紀傳到英國,十九世紀浪漫詩有不少描寫大自然的風景。
愛爾蘭詩人黑倪曾如此表示:「To know who you are, you have to have a place to come from."」要了解你是誰,你必須知道你來自一個地方,你心須有歸屬感。當然,你可以強調超越,但超越者也,是要超越這狹隘的鄉土情懷,例如花蓮情結,但你必須有這麼一個地方去超越,必須先承認你來自花蓮。偉大的作家具有超越性,喬哀思大學畢業後,離開故鄉都柏林,幾乎不再回去;他超越了都柏林,但他必須有一個都柏林能超越。美國小說家福克納 ( William Faulkner ) 是世界級的作家,但他的作品都在抒寫美國南方小鎮。有人說故鄉是我們的祖先流浪的最後一個據點,這說法跟後結構批評觀念一致。故鄉不一定固定不變,神聖不可更動,你可以改變它,但你必須從故鄉出發。相對於所謂「在地詩人」,那種帶著異國眼光的作者就不是。如「我打江南走過,那等在季節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春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就不是在地詩,江南記憶對詩人自己而言也許很真實,但卻非台灣大多讀者的經驗。
黑倪又說:「We are dwellers, we are namers, we are loves, we make homes and search for histories."」我們是居住者,我們是命名者,詩人更是典型的命名者,甚至扮演整個族群發言者的角色。美國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即代表了美國這個新興族群在發言。我們熱愛地方,當然我們也可以恨它,像喬哀思認為都柏林一無是處,整個城市癱瘓著、瀰漫著死亡的氣息。他遠走他鄉,再回過頭來刻劃、批判愛爾蘭。我們創立家園,尋找我們的歷史,歷史並非原來就存在,它等待我們去挖掘並賦予意義。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