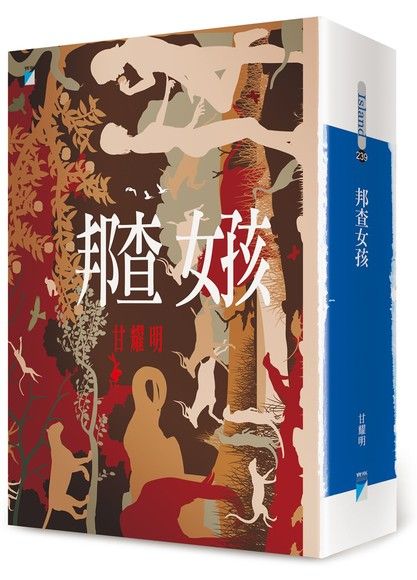
書名:邦查女孩
作者:甘耀明
ISBN:9789864060139
出版:寶瓶
___
內容簡介:
「走了多久?」
「一個太陽,一個月亮,一條河,六個山。」
這是動人的愛情故事,她為他蓋一間學校,他為她犧牲了摯愛。
她是古阿霞,在餐廳梯間躲了五年的阿美族女孩,有一天決定跟花蓮市最有名的「殺刀王」離開。
他是帕吉魯,是電鋸狂飆年代的傳統手鋸伐木工,罹患亞斯伯格症與緘默症的他總是沉默如樹。
為了蓋學校,他們環島募款,進入「臺灣最大杜鵑窩」花蓮玉里鎮尋找神祕的老兵,翻越中央山脈找尋令人深刻的共產黨老師,拜見慈濟人與遭中共驅逐的天主教主教,一路突破困境宛如上帝與菩薩出手幫忙。然而,學校蓋好了,更艱鉅的命運即將考驗他們……
這也不只是愛情故事,更訴說一九七○年代自然文化的迷人故事,呈現中央山脈瘋狂的伐木景象、臺灣山林最後處女地的珍貴、一則攀登聖母峰的生死掙扎、一座藏著傳奇命運的菊港山莊、一隻身分成謎的大山之狗、一個如何在森林大火脫困的互助情誼,這是甘耀明突破《殺鬼》的溫柔之作。
好、厚、的、一、本、書、啊!!!!!!!!!!!
整個年假我有一大半時間都在看這本書還有佩索亞的詩集上了(這兩本書加起來超過1100頁!如果不是年假實在看不完啊啊啊啊)
(提醒,以下評論有劇透,介意就不要往下看了喔)
在看這本書之前,我沒有讀到書封上所寫的「這是一個愛情故事」,但隨著劇情發展,確實會真心感嘆「啊,是個很美的愛情故事呢」,不知道有多久沒看到一個男作家寫好愛情,這點讓我印象很深。
然而,書封上寫「他為她犧牲了摯愛」,這點我就有點疑惑,帕吉魯為阿霞犧牲了什麼?是指為了阿霞蓋學校所以賣掉森林嗎?這點我看不太懂。
這本書把角色命運揉合台灣1970年代的重大事件,以及台灣伐木業的興衰史,細節繁多且極其考究,文字有著自己特殊的魔幻氣息,感覺得出作者的野心。
其實已經有很多人說他們有多喜歡這本書了,就,容我述說我不同的意見吧。我其實有幾段有被吸入故事裡(尤其是最後100頁),但很多時候卻「一邊很清楚這是厲害的小說」,「一邊想,恩好像哪裡不太合拍」。
幾個我自己讀時覺得卡卡的點:
1.劇情前面鋪陳了很多,但後面卻草草收尾,看到最後會有種「蛤,那之前為什麼角色要那麼努力」的疑問,感覺人物的動機淪為劇情發展專用,等劇情發展完角色就可以失憶了。
例如:
(1)阿霞為了帕吉魯蓋學校(不是主因但小說有提及),後來帕吉魯根本沒去學校也只是一句話帶過。
(2)阿霞特地去台北參加五燈獎比賽,後來為了幫助豬殃殃而不參賽。這點真的超奇怪!!!!如果幫助豬殃殃那麼重要,為什麼不是到台北就持續去找豬殃殃,又或者比賽完再去也行,整段文字完全看不出來就是一定要比賽當天去的必要性。
2.突然來一段對慈濟的歌頌(不是說不能寫,但不是用這種直銷公司傳單風格的文字來寫),啊,好出戲。
最後,這部分非批評,而是我個人的感受。
這本書對我來說是很殘酷的一本書,人類為了生計而砍倒幾百年的大樹,黃狗為了取樂而咬死許多小動物,看上去都難以挽回,這讓我持續問著那個問題:「人類有資格這樣無止盡地掠奪嗎」
我想我會痛苦,是因為我知道,那不只是小說情節,而是現在正發生。
D*
___
p.20
她把幾件衣服與書本塞袋子,從床底抽出鈔票,再看看還要拿什麼,這時她的額頭不經意碰到了燈泡。燈搖動,影子晃動讓人以為擺設也跟著晃起來,晃呀晃的,她心頭沾了惆悵,淚眼矇矓。她真不敢相信自己在這待了五年,走與不走都消耗勇氣,但機會一瞬間,她現在終於抓到。
她跑到後門時,帕吉魯沒走。
他走不了的,一群廚房的婆婆媽媽圍著他,問長問短的,包括生辰八字、職業等。蘭姨好急,想在最短時間內榨出資料,她拿鍋鏟,快把抵著的帕吉魯額頭戳出了窟窿,卻逼不出半句話,轉頭問古阿霞:「這啞巴叫什麼來的?」
「不知道。」
蘭姨把聲音提高,接著問:「好,那妳要跟他去哪?」
「不知道。」
「那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不知道。」
「那妳知道他哪些?」
「我今天才在街上遇到他。」
「要跟他走?」
有那麼片刻,無人應答。古阿霞看著蘭姨,說:「管他是風是雨,我抓到就要走了。蘭姨,妳知道的,我就是想走。」
p.28
古阿霞忍不住笑起來,「邦查(Pangcah)就是阿美族(Amis)的意思,我祖母說,邦查是更古早的時候對阿美族的說法。多古早呢?那時候的樹醒着,能走動,有種叫 Pako(過溝蕨)的鳥,停在山谷就變成植物;有種憤怒到皮毛倒豎的蛇 Oway(黃藤)看到一片雲影後,感動得變成藤蔓;那時候呀!有種叫 Lokot(山蘇)的魚爬上岸就貪睡成了植物,那時呀!有一種長相奇怪的魚叫 Palingad(林投),偷偷愛上清風,跳上岸隨之跳舞。那時,巨人『阿里嘎該』的黑色眼淚落地發芽。那時候有多久呢?祖母說,好遙遠了,就像你一晚有好多夢,你只會記得醒來前的最后一個夢,不會想起最早的那個夢,所以要知道那是多久前的時間是想不起來了。」
「好難懂呀!」
「是呀!地球是活的,地球是個夢,一個宇宙中最飽滿的夢境。」
她的眼光從火堆拉回來,比火光還亮,看見帕吉魯看過來,對他說出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話:「我夢到過你,很久之前,那可能在我的第一個睡夢,也許就在名叫 Palingad(林投)的魚爬上岸就變成植物的時候。」
p.86
「如果妳想跟樹講話,就化成陣風;如果妳想跟木材說話,得化成火;如果妳想跟灰燼講話,得化成水,可是要跟人說話,妳也還是個人,處裡人的問題是個難題。」
p.114
有時候我認真想,佛陀與耶穌是不是有精神病,才會幫人,正常的人都是自私的。
p.217
不是每個人都要活在自己想像的圍籬內生活。
p.440-441
「我知道你們不高興,但這是祖靈留下來的方法。」布魯瓦說,「我們得把打到的獵物吃光,吃不完就帶走,不能浪費,不然沒有下一個豐收。」
「我們不能待太久。」古阿霞說。
「阿美族的祖靈怎麽教導你面對食物,如何面對這個山與河?」
關于祖靈與食物,古阿霞最記得巴歌浪(Pakelang)。這是在婚喪喜慶或豐年祭的「句點式聚餐活動」,大家到河邊或海邊抓魚烹食,所有煩惱與不悅都會付之流水,重新獲得力量面對未來。「巴歌浪」後來成了邦查的重要活動,以野菜或魚類的食物洗禮,用聚餐忘卻苦難。
「我們是平地的山地人,不是山地的山地人,」古阿霞強調,「祖靈透過了野菜大餐讓我們忘記煩惱,跟進教堂一樣有效。」
「祖靈跟教堂一樣有效,那上帝教你如何面對這些山與河?」
「我不懂你的意思。」
「日本人來了,他們教會了我們是很殘忍的人,教我們穿上衣服與恥辱。紅太陽走了,白太陽來了,這個政府教會我們是很窮的山地人。我們在這塊大山大水生活了幾千年,才發現自己沒有錢,很苦惱。然後,耶稣來了,佛陀來了,外頭的神明教我們面對苦難、面對煩惱,卻教不會我們的子孫們面對眼前的大山與大河,連佛陀也不會,他們是從很遠的地方坐船來。祖靈才會,可是,祖靈不會教我們賺錢,也不會學耶稣一樣給我們奶粉與糖果。」
「你們就是太懶了,努力工作就好了。」趙坤說。
「我們從來就是這樣生活,沒有懶,後來,我的兒子覺得自己太懶了,要多工作,去跑船,跑到南美的巴拉圭。」
「你很懂外國呢!」
「他死在那,我當然要記得那隻烏龜。」
衆人不知該笑,還是該悲傷。不過,布魯瓦繼續說,把話題拉回了獵殺水鹿的問題。他說,動物與森林一直是太魯閣人的夢,剝奪了夢,只剩黑夜。他們曾經被剝奪了夢很久,甚至剝奪了自己的名字。他又說,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爲他們不斷地「被帶走」。他們原本是住在立霧溪的陀優恩(Doyon)部落,日本人花了兩萬多個士兵,用精良武器,才讓三千個太魯閣人死去,或悲傷到老死。他父親就是後者,最大懲罰是永遠無法拿到獵槍,強迫遷到了整夜被山棕花甜味嗆醒的塔比多居住。接着日本人要他們離開。他們往南走了30公里,走到摩里沙卡開墾,那裡種了什麽都死,他也把死去的父親種在客廳地板下。後來,伐木開發讓族人被迫放棄墾地,遷往萬里溪北岸台地,那裡什麽都種不活,只有石頭種得活。最後,被瘧疾殘害,和附近殘存的部落合住在現在的村子。他們不斷遷村,最後失去了部落名字。
「日本人與平地人拿走了太魯閣人的夢,太魯閣人的獵槍,也拿走了太魯閣人的名字,」布魯瓦說,「卻拿不走這片大山與大河,水鹿是這裡的子民,我們如果多拿了,就應該好好吃光。」
p.676
「我有好多的話要跟妳說,真的,我怕這輩子都不夠用,要用好幾輩子才講得完,請妳聽我說。」帕吉魯苦求。
「我聽,我認真聽。」古阿霞坐得端正,撲哧一笑。
「……」
「怎麽不說了?」
「突然覺得很累,我可以靠着你就好嗎?」
帕吉魯靠在古阿霞肩上,時光安靜樸淡,兩人坐在火車站前的麵包樹下,一如初逢,海風吹來,孩童嬉戲,黃狗繞着噴水池亂叫,春風吹動滿城的樹葉唱歌而代替他們的千言萬語。
從此要講到地老天荒了。
從此是沒有地老天荒了,真的沒了。
因爲,帕吉魯沒有如願離開森林,成了咒谶森林的另一則傳說。他與古阿霞的相遇,是他休克前的一瞬間夢境。這夢境是他付出生命最後能量才抵達的甜白之境,這夢境是他在鋪滿青苔的大岩石回望森林時啟動,他走不動,睜眼看天地一滅,慢慢死亡。他死前以堅定的藕斷絲連在腦海中見到了想念的人,要是古阿霞後來知道這點,她餘生會釋懷。她不知道,又老是想到帕吉魯留在原木上的遺言而做不到。
那隻被帕吉魯驚擾的松雀鷹拍翅,飛出樹冠,繼續往上飛,朝藍天盤桓了幾圈。午後常有的濃霧從山谷升上來,淹過山巒,松雀鷹失去了來時的蹤影,失去森林,失去牠撲飛而出時的帕吉魯位置,朝萬裏溪河谷滑去。
雲海終於形成,台灣東部淹沒在蒼白之中了。
不久,雲海翻過了中央山脈。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