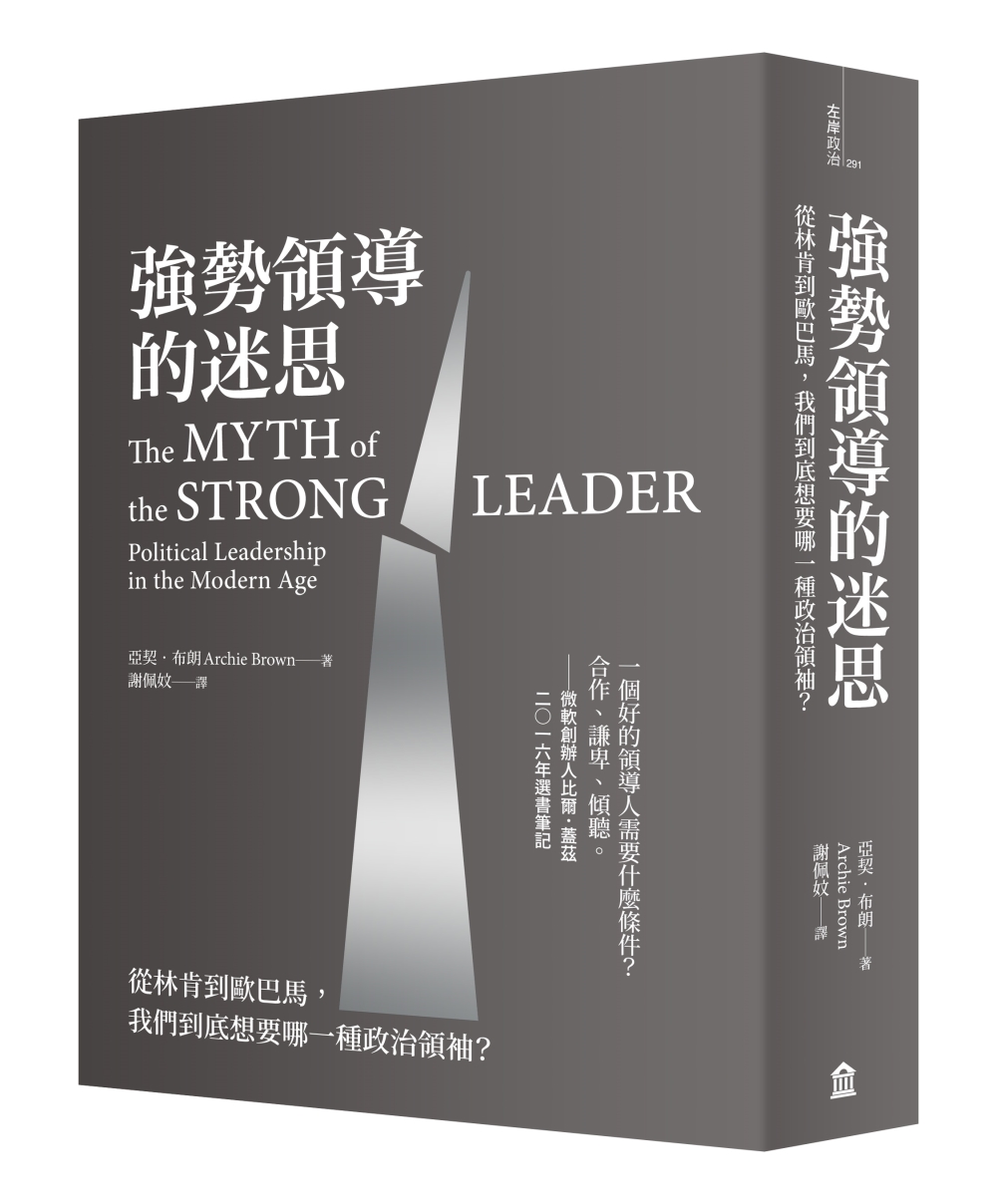
書名:強勢領導的迷思:從林肯到歐巴馬,我們到底想要哪一種政治領袖?(The Myth of the Strong Leader: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the Modern Age)
作者:亞契.布朗(Archie Brown)
譯者:謝佩妏
ISBN:9789865727925
出版:左岸文化
___
內容簡介:
「領袖」該如何定義?一個「幫助團體打造並實現共同目標的人」。——Joseph Nye
我們太常把領導這件事簡化為不是強就是弱;然而,要發揮有效的政治領導,可以說有百百種方式,當然導致失敗的政治領導也是百百種。我們總是責怪某些領導人讓經濟變壞,讚許某些領導人力行社會改革,卻鮮少提出疑問:為什麼有些人會成功有些人就失敗?
牛津大學的亞契.布朗教授研究了過去一百多年來的政治領導人之後,提出一個挑戰所有人常識的看法:那些在決策過程中力壓同儕、不容異議的強勢領導人,就是比較成功,也比較值得讚許的嗎?我們總是認為那些會聽取別人意見的領袖是弱勢領導,但事實證明最願意和別人合作的領導人往往會產生最深遠的影響。
從小羅斯福總統、詹森總統、柴契爾夫人這種把權力往外擴展的領導人,到戴高樂、戈巴契夫和曼德拉這種促成體制變革的領導人,亞契.布朗重新審視形塑了這個世界的各個領導人。他提醒我們不要把過度自負的個人所擁有的過度權力等同於優秀的領導。
其實從標題就看得很清楚,作者認為強勢領導並非優秀的領導,會看這本書就是想看作者如何提出觀點並證明自己的論點。
我看之前有想到作者會舉各種領導人當範例,但我以為會是舉例比論述會是3比7的篇幅,結果實際上是7比3,講各國領導人的內容好~長~~~~~其實可以從資料感受到作者的認真,但對我這種對各國政治陌生的讀者來說讀起來挺吃力的,我覺得這本書適合每個章節開成至少三小時的課,佐以大量圖片、影片、歷史資料,這樣應該會非常有趣。
D*
___
P.4(序)
這是一本論述性的著作,書名即直接點出本書的中心論點。一般認為,傳統定義下的強勢領袖,即獨攬大權、呼風喚雨、主導決策的領導人,就是最受人民愛戴也最成功的領導人,而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戳破這個錯誤認知。這一類的領袖當中有一些人風光得意,但整體而言,政治大權掌握在一人手裡往往導致重大缺失,甚至種下禍害,掀起血腥屠殺。書中也探討了政治領導的其他面向,但我所謂強勢領導的迷思,仍是串連起所有針對民主領袖、革命領袖、威權領袖、極權領袖等討論的主軸。民主領袖之所以造成的傷害較少,正是因為權力受到政府以外的力量牽制。然而,當今民主國家普遍有種危險的錯覺,以為領導人愈能掌控其政黨和內閣就愈成功,而合作型的領導方式反而代表領導人軟弱無能。此外,合作型的政治領導帶來的好處也經常被忽略。
P.9(引言)
雖然不只有一種解釋,但「強勢領導」通常指領導人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上,他/她掌握了大半公共政策及所屬政黨,並做出重大決策。一個人掌握愈多權力,我們就愈該正視他,我認為這種觀念是種假象,無論我們討論的是民主政體、威權政體或介於兩者中間的混合政體。每個國家都需要有效能的政府,但程序也很重要。當一個領導人認為沒人懂得比他多,因而抄起捷徑時,問題就來了,甚至會引發災難性的後果。「正當法律程序」是指,在決策過程中,相關部門的重要成員都要參與。同時理所當然地意味,政府採取的行動應合乎法治精神,並且依民主程序向國會和人民負責。
P.47
有些隨著法國大革命而來的政治創新影響深遠,例如政治「左派」和「右派」(源自法國國民議會的座位安排),以及「自由、平等、博愛」的概念(或口號)。
P.64
很多有關美國的政治研究也證明,「人民會把票投給激發正確情感的候選人,而不是提出最佳政見的候選人。」
P.289
農業集體化在鄉下地區造成極大痛苦,而一九三○年代農民還占人口大多數。然而,即使在二十一世紀,後蘇聯人民被問到二十世紀蘇聯最偉大的領導人是誰時,史達林時常還是名列前茅。由此可見,那些把國家的成功,尤其是蘇聯打贏二戰,跟史達林綁在一起,把失敗、壓迫和暴行都推給其他人的宣傳,發揮了深遠的影響力,在很大一部分人民中心留下痕跡。
P.308
接班問題一直都是困擾威權體制的一個難題,尤其是共產體制。這裡頭有兩個彼此相異但都很嚴重的問題。一方面,當最高領導人指派愈來愈多親信坐上高位,後者又擔心未來飯碗不保而支持他,就會導致執政者在位時間長之又長。另一方面,當領袖不得不換人時,通常是在位者年老病逝,這時候黨內鬥爭可能已經激烈到危及體制的穩定。
P.332
十八世紀的杜爾哥寫道:「專制統治很容易。隨心所欲是一國之君很快就能學會的規則。說服人需要技巧,但命令人什麼也不需要。專制統治若是激怒不了受害者,那就永遠不會從世界上消失。」專制統治確實遲早會刺激受海者戰起來推翻政權(雖然暴力革命往往是另一種威權統治的序幕)。然而,即使是獨裁君主也無法只靠武力統治,因為他必須要能說服周圍的人(他的禁衛隊、軍隊將領或政治警察頭子),讓他們相信效忠他有利於國家或個人利益(更常是兩者都有)。比杜爾哥年長一些的大衛‧休謨認為,「要是一個暴君的權威完全來自恐嚇,就沒有任何理由要害怕激怒他。因為他身體的力量能影響的範圍很小,他進一步擁有的力量一定要奠基在我們自己的想法,或是其他人認定的想法上。」
P.387-388
缺乏正當程序會把更多權力集中在首相及非民選幕僚手中,也會對政策結果造成影響。
(中略)
尤其是旅行和溝通速度大幅提升,現今的首相和總統有更多直接互動的機會,有時也必須代表自己國家發言。因此,他們擁護的政策應該經過民選政府的集體討論也就更加重要,而非更不重要。決定政策的任務不應該留給首相一個人去完成,而是相關部門且能獨當一面的政治家不該迴避的責任。
P.396
馬克斯‧韋伯寫道,政治人物每天無時無刻都要克服「庸俗的虛榮心,這是對腳踏實地追求目標,以及……避免自我中心的致命大敵。」韋伯認為,缺乏客觀和不負責任是政治上「不可饒恕的罪行」,而虛榮心此一「希望自己盡可能站在最前排讓人看清楚的需求」,會誘使政治人物犯錯,「時常有變成演員的危險」,最重要的是,只在乎自己給人留下的印象。
P.407
政黨日漸衰退的同時,其地位將會被社會內外擁有最多財富動員政經資源的人所取代。雖然從十八世紀以來政治和社會都發生了巨大的轉變,第一章引用的亞當.斯密和約翰.米勒的話仍然適切。「財富的權威,」斯密認為,「即使在富裕和文明的社會裡也很大」。他的學生米勒同樣指出,源自財富的影響力「不但比單純的個人成就更大,也更加穩定及長久」。而政黨——工會也是——以其廣大的成員和強大的組織形成一股民主的力量,跟豪門巨富和大型商業與金融組織相抗衡。領導人若是關注後者更勝前者,就可能導致兩種危險的後果。一是國家會愈來愈傾向金權政治,而非民主政治。二是政黨的地位會日漸被直接行動的組織取代。後者往往對民主規範和正當程序興趣不大,容易落入一個世紀前的革命分子所掉入的陷阱,以為只有目的才重要,因此無論用什麼方法達成目的都無妨。即使是為了對抗不公不義才憤而挺身反抗,如中東近幾年來的「無領袖革命」,也有可能因為缺乏民主政黨所具備的完善組織、政策一致性和政治多元發展,而為新的威權體制鋪路。
P.411
最後,強勢領袖下的幾個重大誤解值得再次強調。在議會民主制下,一般人往往誤以為國家領袖的價值高於他們實際的價值。因此,由其他人主導的政策,功勞常由首相(總理)獨享,選戰的勝利也常被誤認為是黨魁的功勞,其實勝選或敗選跟領袖的關係不大。更根本的錯誤是,把高高在上傲視眾人、不顧資深黨員和黨機器、依賴親信更勝於黨的人,視為我們期望看到的領袖。剝奪應該屬於個別部長的權力,或干預更適合讓閣員集思廣益的爭執,無論是政府或政黨內部的爭執,都不應該被視為民主領袖的成功標誌。相信自己有權利主導不同領域的決策,也試圖行使這項特權的領袖,對良好的治理和民主政治都是一種傷害。他們應該得到的是批評,而不是追隨。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